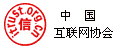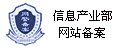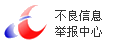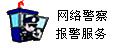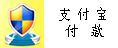试论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文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文学论文发表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学报论文发表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图书馆类论文发表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
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